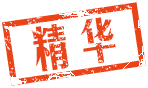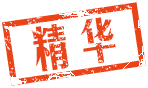|
齐豫,《九月的高跟鞋》。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
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1 十天前我在一个陌生的校园里摔了一跤。那天的秋阳明亮刺眼,照得整个校园空旷惨白。当我发现脚底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台阶(9月的小台阶)时,瞬间不知重心去了哪里。我花了10秒重新定位,发现重心就在不远的前方,于是我慢慢扑地,并且像鱼一样在水泥地上游了出去。 其时我因为达到稳定状态而干脆歇在地上。我有些晕眩,周围有许多陌生的大学生,他们娇嗔地围观我,一个女生娇声说:太吓人了,哎呀吓死人了!那么多学生,没有一个伸手扶我。也许他们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帮助别人的概念,对他们来说,那完全是新概念。 在明晃晃的秋阳下,我成了一条在水泥地上扑腾的鱼——用膝盖扑腾。 这一跤的结果是:当时同时摔破的两个膝盖由于负载不同,右膝盖虽然有一块块乌青,但很快就消退痊愈了;比较糟糕的是左膝盖,灼热疼痛,按下去变得软软的,且发出叽叽咕咕的声音,似乎里面的非牛顿流体在不停地涌动。真是太吓人了! 直到现在,我轻轻把手放在左膝盖上,依然能感觉到那种非线性的涌动。恩尼味,这一跤让我整个假期只能坐在桌前备课审稿和看谍战片,几乎不说话。我选择的谍战片是《誓言无声》。 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原本就不爱说话。从小妈妈就教育我:女孩子要文静!长老后我不爱说话,妈妈以为是她教育的结果,其实根本不是。我就是不爱说话,经常连说话的欲望都没有。 2 我这个不爱说话的毛病,从北卡访学回来后更加剧了。北卡寂寞,常常几天几天地没人跟我说一句话,我却非常享受这样的寂寞和沉默。 寂寞是一种稳定状态,我们都将走向终极寂寞。 我也曾认真分析过自己不爱说话的原因,因为对一个以教师为职业的人(我还是年年过教师节的呢)来说,不爱说话可不是一件好事。通过分析,我认定了那是因为我有一种信念:说废话可耻!这个信念达到极致,以致于在课堂上我经常会累得讲不动课。我要确保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都不是废话,就必须多准备很多内容,所以填满一次课的内容让我在下课时精疲力尽。我总是很羡慕那些上课轻松的老师,我不知他们哪来的自信认为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废话。这些废话也许无害,也许只是啰嗦而已,但我就是做不到讲废话,我没有那样的自信。 可想而知我是个嘴笨的人,很笨很笨。我不会说那些世俗的俏皮话(这一点我特别仰慕郭德纲,在郭德纲与吴秀波共同主持节目时,吴秀波总是显得那么嘴笨),因为它们是废话;我不会说一些励志的鸡汤话(这一点我特别仰慕希拉里),因为它们是废话;我不会跟人斗嘴(这一点我特别仰慕伶牙俐齿的颜美女,她说饶老师跟她斗嘴从来没赢过),我认为那些也是废话;我还不会说客套话也接不了别人的客套话,因此总是憨憨地沉默,只剩了一点笑容,真切地表达我嘴笨的愧疚。除了这些,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说我确认不了是否正确的话,因为我认为它们不能给人带来帮助。 所以,能留给我说的话实在不多,因此我是个嘴笨的人。我是个嘴笨的人,并且从不喜欢自称口才好的人,不是因为嫉妒,我知道所谓的口才好,无非是以上那些我不想或不会说的废话,他们能充满自信地说而已。 然后我把所有的废话写成文字,或者把它们扯进梦里,跟你细细密密地诉说。而你听着我的废话在我的梦里进进出出,冷漠或温柔,清晰或模糊,裹挟着我的泪,从梦境到现实。 3 这个夏天开始之前,我接收到了一个中科院在物理所办的叫“科学咖啡馆”的邀请,说是他们很想让我去做一期沙龙。我赶紧说我不是学术大牛(只是菜鸟,还是老菜鸟),不敢去参加这样的沙龙。可他们说这沙龙不是纯科学讲座,就是搭建一个科普交流平台,介绍、推介、传播、探讨科学“新思想、新动态、新理论、新方式”等。他们说特别想邀请我去参加,我心里暗暗叫苦,估计他们以为我的文字表达还可以,就推断出我的口才也是不赖的了。 行文至此,我就想说明自己是一个嘴笨的人,很笨很笨。我是一个嘴笨的人,却(由于责任)不敢推脱那些真正需要我去说话的场合。只是我需要用比口才好的人几倍的精力去准备一次说话,让人们觉不出我的嘴笨。这是我很少去做讲座或报告的原因——真正重要的东西,没必要到处去吆喝! 上面一段说明了我接受这次沙龙活动邀请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活动重要,而且只此一回,下不为例。他们没有强制时间,而是很贴心地要了我一个可以参加的大概时间。于是我先给自己留出长长的准备时间,我不敢说是因为自己嘴笨,而是说我先要去背咖啡。 说到咖啡,是这个活动的副题。“科学咖啡馆”要求每一期沙龙的主讲人要携带一种咖啡豆作为当次活动的主打咖啡,并以自带的咖啡为主题作一个简单的交流,请大家品尝。这相当阳春白雪,活脱脱“科学闲人”的模样——喝着咖啡晒着太阳聊着科学。我喜欢!老实说我不懂咖啡,但要编一个关于咖啡的阳春白雪的故事,对我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 于是我就真的背咖啡去了。我给他们说的大概日期是7、8月份,是因为6月初我有一次去西雅图的旅行。我去了西雅图的Pike Place Market,在那里的第一家Starbucks买了一包咖啡,然后背回上海。 我想,这足够我编一个故事了吧!其实不用编,那天暮色四合的时候,我坐在港口吹风,想着我们梦里的纠缠,前世今生,等也等不回来的水手,我热泪盈眶。 在梦境里,我是那个有着化解冰雪的容颜的女子,抚着膝盖一直守候在这个港口,只想等到你能看一眼我的容颜。 4 这篇文字不能这么一直写下去,因为全是废话。这是一个令科学家们激动不已的季节,大家都在关注和谈论诺贝尔奖,而我却如此煞风景地跑出来写一些对社会进步没有意义的文字。 “你能得诺贝尔奖吗?” “你做的是诺奖级的科研吗?” “你跟诺贝尔奖沾得上边吗?” 我承认我沾不上边。却是一个不断地呼吁一个养“科学闲人”机制的人,因为我就是冲着自由懒散随心所欲的工作才进入学术圈的,却逐渐发现这是个人管人的圈子,今天特别喜欢被管被考核的那些人,明天就成了特别喜欢管人的人,张着一嘴白厉厉的牙齿,数着你的论文项目影响因子引用次数工作量,为了能在别人的考核单上狰狞地划上一个血红的叉而充满快感。 科学家如果失去了自由思考的时间,就不会有自由灵性的科学思想和成果。肯定确定以及一定! 所以说回那个我还没有去赴约的“科学咖啡馆”沙龙,写这篇博文,其实是表达自己已经过了约定时间却还未践行的负疚心理,也表达了自己没有忘记曾经的约定。其实我在夏天来临的7月已经去北京化工大学参加了一次学术沙龙(我很喜欢那样的学术交流形式,也许会另文着墨写一写,也许不会),因为那次活动是限定了时间的,所以践行了。 而关于这个充满懒散自由咖啡香味的“科学咖啡馆”沙龙,我想我还是会赴约的,请容我这个嘴笨的家伙编好关于咖啡的故事,准备好我怯生生的浅薄的科学思想,再赴京与你们约会吧! 但这包咖啡豆我只能废弃了,行家们都知道,科学历久弥香,但咖啡过期作废。
科学历久弥香,咖啡过期作废 |